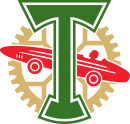曼联旧将帕克袒露心声:被基恩调侃内裤事小,当代足球丢失的血性才真该警惕
- 时间:2025-12-17 13:49:57|
- 来源:网络转载|
- 人阅读
前曼联边后卫谈现代足球让他反感之处:青训学院愈发“中产化”,以及走进监狱发声的经历。
在赢得首届英超冠军约10年后,一位纪念品收藏家找到了保罗・帕克。此人想要收购一座迷你奖杯——那个赛季,曼联夺冠阵容的每位成员都收到了这座奖杯,而非传统的奖牌。帕克不愿出售。对他而言,踢球的意义就在于夺冠,他绝不会舍弃这份见证自己首个重要成就的实物纪念。然而,当他表达拒绝之意时,买家为说服他而开出的高价,却让他颇感意外——尽管这努力最终仍是徒劳。
“那笔钱数额不小,”二十多年后,帕克回忆道,“但他接着说,要是埃里克(坎通纳)的那座,他愿意出三倍的价。”
这便是边后卫的宿命。当足球历史被书写时,聚光灯与光环永远属于前锋,边后卫不过是陪衬。但帕克却是两支开创足球新时代球队的核心成员:曼联终结26年冠军荒、夺得首届英超冠军时,他在队中;次年球队历史性斩获双冠王时,他依然在列。
他同样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英格兰队杀进半决赛的关键一员——正是那支队伍让足球重新成为潮流。因此,当他在伦敦一家咖啡馆与《每日电讯报》体育版记者会面时,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出:若当年的曼联与英格兰队同场竞技,哪支队伍会胜出?
“要我说,当年那支曼联身体对抗更强、作风更硬朗。这正是球队成功的关键:我们从不会被吓倒。”帕克说道。
他的话不无道理。人们或许总能想起坎通纳的霸气张扬、吉格斯的闪电突破,但那支曼联实则是一支“肌肉军团”——从史蒂夫・布鲁斯、加里・帕利斯特的后防搭档,到罗伊・基恩、保罗・因斯的中场组合,再到马克・休斯领衔的锋线,这支队伍从不会在对抗中退缩。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如今球员稍有碰撞便夸张倒地、仿佛遭受重创的习惯时,帕克翻了个白眼。
“你这问题可算问到点子上了,”他说,“这太让我生气了。现在看球,我总觉得这些球员毫无羞耻心。前几天看一场比赛,有个球员为了让对手吃黄牌故意摔倒,我气得直接换了台。在我踢球的年代,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。”
他回忆起1993-94赛季曼联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与温布尔登的足总杯比赛——这段比赛的高光片段如今常被分享在社交媒体上,用以对比今昔足球风格的差异。
“你们去看看那段录像,”他建议道,“文尼・琼斯曾对埃里克使出一记凶狠的剪刀脚,摆明了想废了他的腿,那铲球太恶毒了。但埃里克倒地后立刻起身,整了整衣领就走开了,那神情仿佛在说‘就这点本事?’。之后约翰・法沙努对我下了同样的狠招,我也是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,下次球到他附近时,我直接撞了回去。和埃里克一样,他倒地后也马上站了起来。这就像街头斗殴:你要是倒地不起,他们只会得寸进尺;你立刻反击,才能让他们知道你不好惹。可现在呢?如今的球员只会在地上滚来滚去哀嚎,太丢人了。”
帕克表示,在曼联,这种不服输、不被吓倒的精神是在更衣室里“炼”出来的——尤其是基恩,总能让每个人保持警惕。
“罗伊就是罗伊,你只能接受他本来的样子,也必须接受。哪怕在电话亭里,他都能挑起一场架。”他说,“我记得有次比赛中我漏了一次铲球,紧接着他就来了一记凶狠的抢断,然后转头冲我吼:‘难道还要我替你干活?’那时候他就要求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”
“和罗伊共事,每天都是考验。他甚至会因为你穿的内裤不好看而找茬——不是他真的在意内裤,而是想看看你的反应:训练时你会不会怼回去?如果你无动于衷,他会觉得你软弱可欺,然后变本加厉;如果你真的反驳,他又会嘲笑你上钩了。跟罗伊打交道,你永远赢不了,怎么做都不对。但我就欣赏他这一点。他现在也没变,我们偶尔还会联系。每次我打电话给他,他总会说:‘你找我肯定有事吧?’说实话,他通常是对的。”
若不是队友们时刻“鞭策”他,那“施压”的人便是教练了。帕克认为,自己能在两位足坛传奇教练麾下效力,实属幸运——但这两位教练都绝非善茬。英格兰队时期的博比・罗布森爵士意志坚定,但其战术指令有时却不够清晰。
“他总叫我‘丹尼’,因为有个叫丹尼・托马斯的球员和我一样,是个小个子黑人。”帕克回忆道,“有次训练练角球战术,他说:‘丹尼,你去那边。’我没动。他又喊:‘丹尼,我都说了,去那边!’我还是没动。他当时就火了。这时唐・豪(当时的英格兰队助理教练)说:‘教练,他叫保罗。’罗布森接着说:‘我知道,但他还是得照我说的做,不是吗,丹尼?’”
而在曼联,他的主帅是他口中“球员管理大师”——弗格森爵士。帕克认为,弗格森的一言一行,都是为了让球员发挥出最佳水平。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的,是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生涯末期时,弗格森采取的处理方式。
“1996年我受了伤,加里(内维尔)当时正在崛起,我因为得不到机会而心怀不满。说实话,我坐在替补席上看着他们不断夺冠,内心深处甚至盼着他们输球。任何处于同样境遇的球员都会有这种感受。所以我知道,我的曼联生涯该结束了。在我看完他们赢得足总杯决赛后的那个周一,弗格森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他说:‘保罗,我真的很想留下你,发自内心地想。但球队需要向前看。我也想讲感情,但我不能——因为感情用事可能会让我丢掉工作。’”
“他的表达方式太得体了,直接、坦诚,又不失尊重。现在我和别人聊起这些事时,还总会想起他当时的处理方式。”
帕克认为,自己能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中立足,与成长背景密不可分。正如他在自传新作《Tackling The Game》(《挑战赛场:我的足球人生》)中所写,他早已习惯为自己争取权益。他出生于伦敦东区,年幼时父母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机遇,举家搬到埃塞克斯郡的达格纳姆。但他们当时并未意识到,那里正是英国国家阵线(极右翼组织)的活跃地带。
“我成长的环境里,周围都是金发碧眼的人,我是当时唯一的黑人孩子。做任何事都要面临挑战,凡事都得靠拼。”
更何况,他一直是身边人中个子最小的。从能跳赢比自己高15厘米的球员的惊人能力,到毫不留情的竞争本能,帕克表示,自己的人生始终被一种“证明自己”的渴望驱动。而那些挫折与侮辱——比如有位青年队名帅曾用带有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词汇贬低他——都成了他证明他人错误的动力。足球,为这个不得不时刻抗争的少年提供了完美的宣泄出口。
“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了。如今的球员并非在街头长大,足球学院想要的是顺从的孩子,是运动员,而非有个性的人。他们对课堂后排那个像加斯科因一样调皮、朝老师扔橡皮的孩子毫无兴趣。作为一项运动,足球正变得越来越‘中产阶级化’。”
而且,最好别在他面前提“球员家长”这个话题。
“我在富勒姆当学徒时,父母忙着工作,根本没时间送我去训练。我得自己坐公交去,下车后还得一路狂奔回家,免得遇上国家阵线的帮派。”他说,“现在呢?家长开车送孩子去训练,还在一旁全程观看。我曾短暂担任过托特纳姆U15梯队的教练,每次训练结束回家,都会收到五六条家长的消息,问‘我家孩子表现怎么样?下次比赛你会选他吗?不选的话为什么?’这种日子我只坚持了一个赛季。我觉得自己是来当教练的,不是来做心理咨询的。”
如今61岁的帕克,除了偶尔担任赛事评论员、每天至少在健身房锻炼90分钟外,他认为自己最有意义、也最有趣的事业,早已与足球无关——他每年会去监狱好几次,为囚犯们演讲。在与记者会面的前一天,他刚去过伦敦东南部的泰晤士河畔监狱。
“我做这些演讲是因为我喜欢,”他说,“有人问我是不是为了钱?我分文不取。而且我通常得在早高峰时段赶路,连老年铁路卡33%的折扣都用不上。”
他坦言,这种演讲并非易事。囚犯们可能是最难应对的听众。“每次开场都很难。一屋子的人,对你毫无反应,气氛冰冷得很。得花点时间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。你得找到能触动他们、引起他们兴趣的点。”
而这个“点”,几乎总是足球——以及他遇到过的那些足坛人物。他承认,自己的足球生涯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沟通平台。
“我第一次去监狱时,刚走进来,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男子——年纪比我大些——看着我说:‘你是保罗・帕克吧?’我当时心想,这下麻烦了。结果他接着说:‘你在女王公园巡游者踢球的时候,我可崇拜你了。’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影响力。因为我的身份,他们或许会愿意听我说话。我或许能改变他们,给他们一些方向,让他们更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或许能真正帮到他们。不过话说回来,现在很多年轻囚犯可能都不认识我了。”
但很快他们就会了解——帕克的演讲通常长达两小时,结束后还会与听众逐一交流。
“我从不会问他们为什么入狱、判了多久。如果他们愿意说,自然会告诉我。大多数人确实罪有应得,但那里有太多被浪费的天赋了。我渐渐明白,他们和我没什么不同。对很多人来说,只是因为那一个瞬间、那一个错误。任何人都可能失足,说真的,我当年也差点走上那条路。”
但幸运的是,他遇见了足球 —— 而足球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圣吉罗斯vs亚特兰大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巴黎圣日耳曼vs纽卡斯尔联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埃因霍温vs拜仁慕尼黑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那不勒斯vs切尔西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帕福斯vs布拉格斯拉维亚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摩纳哥vs尤文图斯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曼城vs加拉塔萨雷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法兰克福vs热刺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利物浦vs卡拉巴赫 全场录像回放
- 01月29日 欧冠第8轮 多特蒙德vs国际米兰 全场录像回放
- 太阳126-117篮网,布克24分,狄龙27分、小波特空砍23分
- 新的时代,东契奇生涯首夺全明星票王,此前10年詹姆斯7次夺魁
- 北伐初见成效,快船一波六连胜后反超灰熊杀入附加赛区
- NBA战报:快船110-106奇才取NBA6连胜,哈登36+7+9
- 从输16分到赢17分!詹姆斯的转型定位逐渐清晰,他决定湖人的上限
- 湖人大胜猛龙!三核轰74分,联防立功,拉拉维亚又开始拉了!
- NBA球星麒麟臂有多离谱?锡安手臂比大腿粗 奥尼尔手臂像充气
- 记者:鹈鹕对琼斯和墨菲分别要价2首轮和3首轮+年轻人,勇士均有意
- 湖人惨败国王!东契奇空砍42分,詹姆斯艾顿效果不佳,众配角打铁
- 雷迪克终于看明白了!发布会爆赞蒂米和范德彪作用,早干嘛去了?